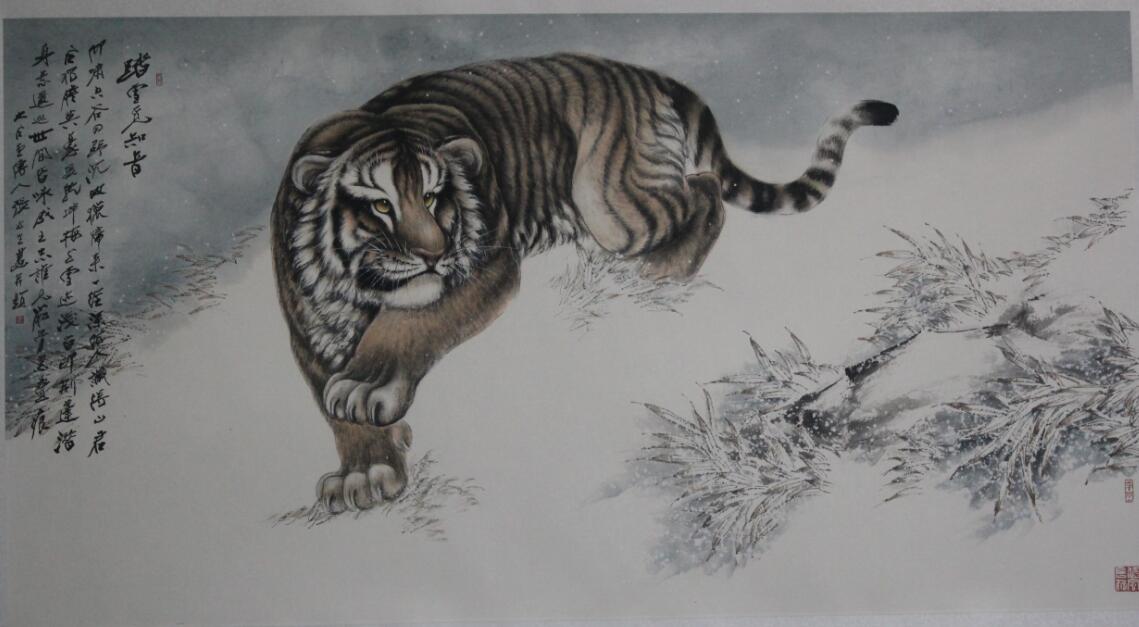宋元时期徽州宗教发展的世俗化倾向
宗教是对人生的一种追问和拷问,而世人对今生和来世都很关心,所以宗教信仰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徽州的佛教和道教在隋唐五代时期,曾经有过一个繁荣的阶段,不仅寺院道观建筑众多,而且出了一批名僧、名道,并对老百姓的生活行为模式产生重要作用。到了宋元,由于新安理学的兴起,在徽州宗族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佛教和道教逐步被削弱,走向世俗化。及至明清,徽州宗族社会高度成熟,佛教道教思想被边缘化。民国时期的许承尧就说过:“徽俗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 徽州宗教发展的世俗化和边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这对徽州社会的研究极为重要,是徽州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就目前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对宗教世俗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当代宗教状况的分析和对宗教未来发展趋势的探讨,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宗教世俗化倾向的文章不多。 宋元时期,是徽州宗教发展的一个转折期,宗教由出世转而入世,向世俗化转型,本文就这一时期徽州宗教发展及其世俗化进行探讨,以求对中国宗教世俗化进程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徽州宗教世俗化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徽州最早见于记载的寺院为东晋太兴二年(319年)所建的休宁县万安南山庵,佛教传入时间当在此之前。隋唐时期,寺、院、庙、庵、堂、塔大兴,《新安志》记载徽州六县唐代寺院达89处之多。道教是我国本土产生的宗教,源于自然崇拜、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神仙信仰、追求长生不死成为促进道教发展的动力。而这一切都与老百姓的生活信仰密切相关,道教在民间的发展,也成为一种潜移默化和自然而然的行为。叙述道教在徽州的形成及其宫观建设,已很难找到准确的文献记载时间。《新安志》中记载建于唐时的道观不到10处,但记载民间信仰的庙宇却有40多处。宋元时期,徽州宗教虽然新建有93处寺院宫观,但宗教活动本身开始向世俗化转型。
徽州宗教之所以在宋元时期快速地向世俗化转向,既有其本身的原因,更主要的则是由徽州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1.佛、道本身具有入世的一面
从表面上看,佛、道讲出世,实际上佛、道和儒家一样,也有入世的特征。佛教修行的个人终极目标是超越世间种种烦恼与痛苦,但人世间总是充满了财、色、名、食、睡五欲,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只有让世俗的五欲六尘生厌、离欲、灭尽,才能达到解脱清净,即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超脱人世凡尘,所以带有强烈的出世色彩。同样,道家讲修炼,要超然世外,隐居潜修,无拘无束,羽化成仙,也是以出世为最高境界。
但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生活在人世中,不能不关注现实社会人生。观音菩萨解救现实生活中众生的种种苦难,满足众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和要求,就具有入世的特征。道教要求修道者必须在社会生活中积功累德,才有长生成仙的希望,同样具有入世的倾向。尤其是它们积极参与政治,利用统治阶级来扩充本教的势力,这就使宗教与政治有了直接的联系。北周武帝“兴道灭佛”,佛教徒就助隋灭周;道教徒借教祖李耳与李渊的关系,李渊便尊道教为三教之尊。儒家讲入世,但儒家思想在历朝立国过程中一直没有起到过决定性作用,在治国过程中又一直被置于利用的位置。原因主要在于儒家“六经”文字艰深,晦涩难读,学者却步,难以在民间普及,统治者不便于利用儒家思想来统治民间。佛教禅宗主张“佛就是我,我即是佛”,只要“顿悟”,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人人即可成佛,真是太简单了。僧人以说故事的方式来讲解佛教经典,佛教教义也就容易渗透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至于道教,直接就是民间信仰的一种集合。唐代徽州道士洪贞起义,北宋方腊自称“得天符牒”造反,在民间都很有号召力,就是很好的说明。
2.徽州教育发达促使佛、道的边缘化
宋元时期徽州教育急速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促使了佛、道的边缘化。北宋著名的儒家思想家范仲淹向朝廷建议兴学,推广儒学。庆历四年(1044年),诏令天下郡县建学,并更定科举法。
徽州的郡学唐代就有,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本府在唐,郡县皆置学,故前志载州之庙学自唐及宋在城东北隅是已。” 宋代,州学一再搬迁重建,规模不断扩大。除州学外,六县县学也相继设立。歙县县学建于南唐保大八年(950年),学址在县南。宋初,因歙县是州治所在地,县学附于州学,不另立,黟县在宋初就有学。祁门县学建于宋端拱年间(988年~989年),知县张式建。婺源县学原来在县城西,休宁县学原在县城南一里。庆历四年(1044年),诏令建学时,均在县城东重建,绩溪县学也建于此时。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教育程度和学术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两宋,徽州共有书院18所,按照《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的统计,宋代全国书院总数约400所,徽州18所占全国总数的4.5%,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元代,徽州除了对宋代的一些书院,如紫阳书院进行重建之外,还新建书院25所。元代大部分时间科举中止,迫使大量儒者另谋出路,很多儒生转向讲学教书为业,这对徽州的普及教育起了很大作用。
蒙学教育是徽州教育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一大批理学名儒不图仕进,热心训蒙事业,坐馆教学。出现了一系列私家创办的蒙学教育机构,如家学、塾馆、塾学、家塾、义学、义塾等,元代是徽州蒙学教育最为繁荣的时期。元时学者赵汸,对当时徽州的读书情景有一句典型的话:“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后来《婺源县志》将这句话归纳成“十家之村,不废诵读” ,由此可见徽州蒙学的发达。

3.新安理学对佛、道的排斥
南宋,新安理学兴起。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该学派由徽州籍理学家为主干组成,奉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朱子学为基本宗旨。朱熹早年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在他有了自己的思想以后,以儒为宗,旁及佛、道,圆融三教,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竭力排斥佛教、道教。他曾说:“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求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尤其性与用不相管也。异端之害道,如释者极矣。” 类似上述言论,在《朱子语类》中随处可见。朱熹不仅依据佛学,从道理上分析批驳佛教,还在政治活动中排斥佛教。朱熹在任同安县主簿时,就曾禁止妇女当尼姑。在向孝宗上书时,称老子、释氏之书都是一些无用之书,认为佛教、道教不足以成事,斥责禅学悟人是断绝人的思考。朱熹的排佛言行,对弘扬儒学起到重要作用,新安理学家既然以朱子学为学派宗旨,必然事事处处排斥佛教、道教。
4.徽州宗族制度将儒家思想渗透到了民间基层,并善于利用宗教为宗族服务
近世宗族制度以尊祖、敬宗、睦族为宗旨,根据儒家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家法,约束族众。徽州先贤程颐、程颢和朱熹尤其重视宗族伦理,朱熹还撰修《家礼》等书,制定了一整套宗法伦理的繁礼缛节,用以维系与巩固宗族制度,并编纂有《婺源茶院朱氏世谱》,推动和促进了徽州宗族制度的形成。
徽州宗族聚族而居,坚持等级制度和主仆名分,重视修墓建祠,注重恤族,强化族众凝聚力,同时注意用儒家思想规范族众的道德行为。主要体现在忠义、孝顺、友悌、勤劳、节俭、礼貌等族规中,这是维持家庭和睦相处以及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对一些不良行为,如闲游、迷信、赌博、嫖娼等,族规也规定禁止。对族中有关祠堂、祖坟、祭祀、族田、修谱等与家族成员有关的各项事物,都有家法族规予以明确规定。涉及家族与外族、地方、国家的关系,也要求子孙要遵守法纪、睦邻乡里。不少家族对族人为匪作盗、参加会党和出家为僧、为道予以制裁。
宗族制度将儒家思想渗透到了民间社会的最基层,使得宗教信仰在宗族制度的排挤下,难以生存。同时,宗族还善于引导宗教信仰千百年来在民间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寺院宫观和僧道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利用他们为宗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