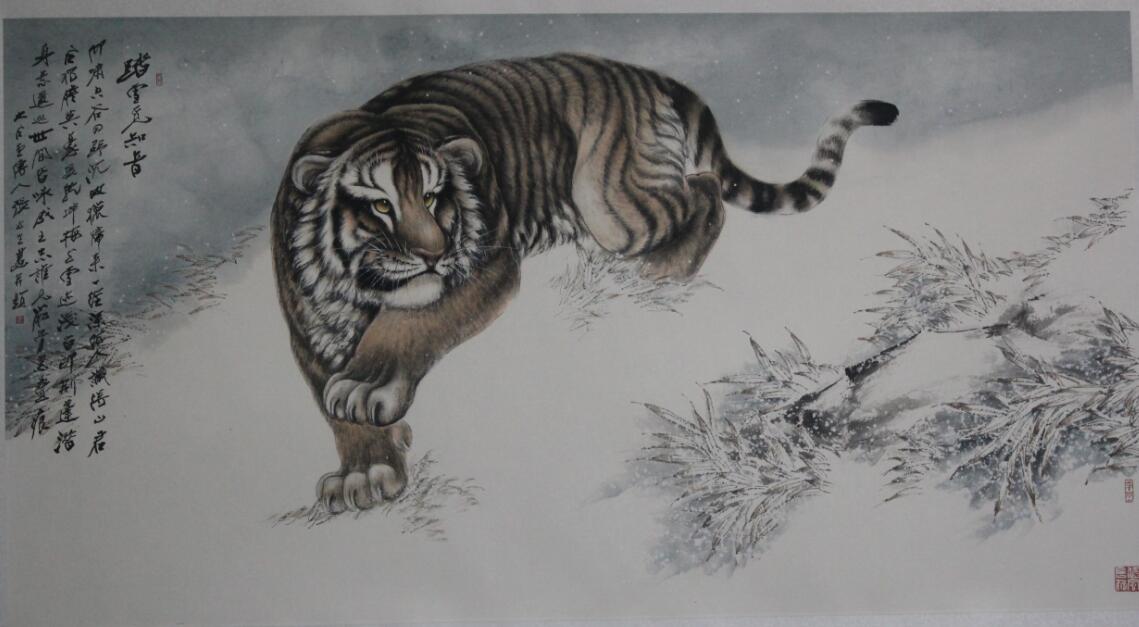证监系统离职官员处级以上多进基金券商等机构
递交辞呈之前,程苏考虑了很久,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决定。他现在的这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体制内、收入稳定、有地位、有时间兼顾生活,而且所做的事情会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很快发现,在体制内想做点事非常不容易,“责任很大,还要承担风险。”
程苏硕士毕业后来到证监会主管下的一家机构。他所从事的工作能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市场数据。以往领导向他索要数据,他都会尽力帮忙。但从2014年开始,他不敢这么做了。“对不起,按照规定我不能给你,如果一定需要请让证监会发个正式的函给我。”
就在今年7月,他向单位递上了辞呈,像他这样选择离开的年轻人还有很多。记者根据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各地商品交易所、中证登、相关协会及研究机构等官网上刊登的招聘启事粗略计算,近期这些机构需要添补的空缺职位超过200人。实际上,这是一波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证监会系统离职潮。主动离职的人里面,还有数十位处级以上官员。
离职
“监管对象的收入是我们的10倍”
工作一年之后,程苏开始感受到体制施予他的压力。
收入的差距首先浮出水面。“有时候和一些基金经理聊天,明明自己和他能力相当,甚至比他还好,可是他一个月拿几十万,我一个月就拿几千块。作为监管者,监管的对象收入是我们的10倍。”程苏说,这样的落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肯定会心里不平衡。
而且,在眼下央企的“降薪潮”之下,程苏所在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收入也都有所下调。今年1月,证监会开始实施的降薪方案就覆盖了程苏的领导们。这些包括理事长、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由证监会直管的干部,在薪酬调整之后,薪资甚至低于各个业务部门的总监。
程苏觉得,虽然大多数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比如他自己,在30岁之前不太会看重薪酬,更看重自己的成长,但是和体制外的同龄人相比,这一点的落差也是很明显的。“在机关里,我觉得个人价值的增值非常缓慢,而且自己不能把握,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想干事情就能干得了的。”
体制内的生活波澜不兴,旱涝保收;而与此同时,同龄人正在市场中拼搏。程苏的一位同事早早就离职去了一家信托公司,后来聚会时程苏发现,这位同事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由于新的工作与以前的工作完全不同,这位同事两年的工作经验并没有得到认可,在新的公司拿着和应届生一样的薪水。但对方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北京、上海来回奔波,“虽然很累,但看得出他很充实”。这更坚定了程苏离职的想法。
去处
“转投基金、券商,年收入几百万”
和程苏一起离职的还有几位同事,他们都是入职两三年后离开证监会系统,去了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券商、基金公司、信托等。
目前程苏在一家国内金融机构工作。刚来的前两周,他几乎天天要加班到深夜。“在原单位我的工作相当于是后台,新的工作在前台,几乎是重头再来。”程苏似乎很享受现在的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独立完成了一个大单。
相比程苏这样的年轻人,证监系统处级以上官员的离职往往会被更多人关注。2015年7月10日,博时基金发布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其新任总经理是2015年1月从证监会离职的江向阳。离职之前,江向阳担任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办公室(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
基金公司是很多证监系统离职官员的新去处。据华夏基金2015年8月1日的公告,该公司总经理汤晓东是2014年8月从证监会辞职的,之后任华夏基金公司督察长;而现任的华夏基金督察长周璇曾经任职于证监会基金部综合处处长。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排名前50位的基金公司中,有证监系统背景的高管就有40多人。
“对于证监系统的人,一般基金公司都喜欢用领导层,对于只有两三年工作经验的人,其实价值并不大。”一家基金公司的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不仅仅是基金公司热衷于启用有证监会背景的高管,券商也偏爱这类人才。
不完全统计显示,有近20位现任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副总裁、独立董事以及中层干部,此前都有在证监系统工作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