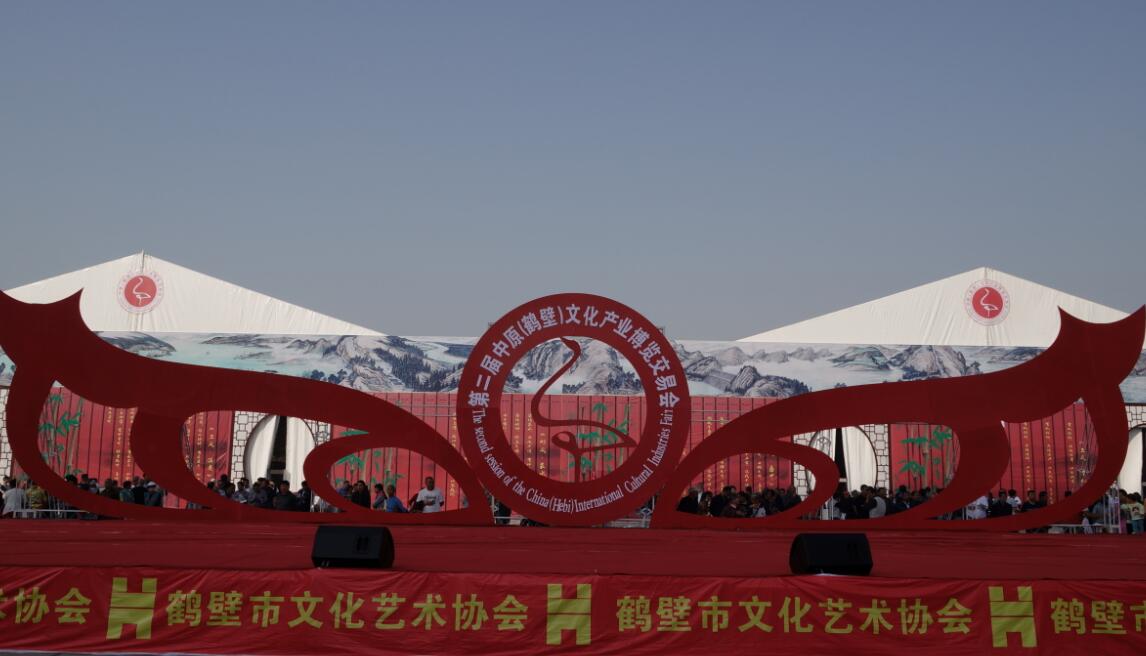欧洲面临危机时 博物馆将再次体现文化认同
 十月,难民跨越希腊边境进入马瑟多尼亚,排队等候进入难民营
十月,难民跨越希腊边境进入马瑟多尼亚,排队等候进入难民营对当今的英国媒体来说,“欧洲”这个词后面不跟上“危机”反倒很罕见。英国是否有可能退出欧盟,这个问题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政治观点。然而,上个月巴黎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加上最近在地中海沿岸、欧洲大陆东端、通往英国的门户加莱……这些地方发生的一幕幕,让“危机”这个词都显得捉襟见肘。当人们以二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流动,欧洲的同情心、行动力和其之所以为欧洲的自信,都受到了深重的考验。欧洲正处重重压力之下——无论是当今欧洲经济计划,还是说我们个人与集体作为欧洲人的文化认同。
在此背景下,讨论博物馆的角色,以及我们更宽泛的文化领域,看起来就有些多余了。在人们的生活、生计与未来都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讨论过去几百年间的艺术和物品又有什么意义?可是我认为,它们同当今世界密切相关。而且,我相信欧洲的博物馆有义务成为团结协作的模范,展现文化交流与理解所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这能为我们带来希望。
启蒙时代
要是有人想理解欧洲的历史,研究重点放在国家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有它能够以丰富生动的细节表明,国家与民族所梦想的宏图伟业。大英博物馆,启蒙时代之子,清晰地描绘了大英帝国的世界观;而卢浮宫,则把伟大的国家作为其宇宙的中心;另外,人们恐怕也找不到比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那些博物馆更能展示奥匈帝国气象的了。
叶卡捷琳娜为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奠定了基石,她在此汇集了全欧洲的收藏,包括来自德累斯顿的沃尔博尔(Walpole)和布吕尔(Brühl)的收藏。在德国19世纪革命时期,“博物馆”意味着在公共空间担纲重任。例如,纽伦堡国家博物馆,早在1850年代就预示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而走进马德里、布拉格或华沙任何一个陈列古代绘画大师的展厅,欧洲,就立即呈现在你眼前。
共同的身份
对欧洲所遭遇的每一次重大危险或变革,都有一个博物馆能将当时发生的故事娓娓道来。1871年统一之后的意大利、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和冷战结束之后的中欧……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博物馆。而每一座博物馆的建立,背后都是在迫切希求建立稳固而共同的“欧洲”身份。
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也不是例外。我们凭借海量的馆藏,接过启蒙运动的火炬。游历在藏品之间,能使我们了解到更多欧洲的故事。
凡尔赛宫的独特影响,在整个欧洲无数的物品中都得以反映,但凡尔赛宫本身的作品则被大革命扫荡一空。博物馆曾为欧洲的身份认同与思想建构作出过重大贡献。欧盟之父让·莫内曾说过:“要是我能让欧洲从头来过的话,首当其冲我要做的就是文化”。这只是美丽的虚构;而博物馆反映出了我们事实上拥有的共同且多样的欧洲身份,这是无法否认的。
然而,只有放在欧洲(实际上也包括了全世界)的语境中,这些藏品的当代价值才能得到忠实的解读。对我们来说,要想成功地让藏品与世界发生关联、相互沟通,学术群体应当像我们的藏品一样多样化、国际化。而且,我们讲述的故事必须要能走得更远,而不再限于我们自己,或那些能亲临现场的参观者。
作为德国人,我常感到自己是一名欧洲人。因为德国20世纪的历史,我在年轻时拒服兵役,也从未感到自己对德国的认同要高于欧洲。当我与英国的同龄人交谈时,他们用“欧洲”这个词的方式同“经济”、“生意”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我同我的法国朋友交谈时,他们毫不怀疑“欧洲”是一个绝妙的概念,同时法国则一直是他们的焦点。我们的博物馆表明了,这些观点都能够通行无碍,但没有某个单一的观点能孤立出来,闭锁在民族的界限之中。这帮助我们体认欧洲的深度、多样性、持续不断的进步,最终,也就让我们看到欧洲作为自信而积极的整体的潜力。
共同的悲剧与胜利
穿过我们崭新的“1600-1815年的欧洲”系列展厅,我看到了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同事们正在准备各种技术装置,听到人们在设立展柜时说起了德语和葡萄牙语,还看到了策展人与专家正在检查一件俄罗斯的壁炉(1800年在莫斯科附近用钢铁蚀刻制造,具有泛欧陆新古典主义风格,2014年在伦敦得到清理和保存),还看到了在马德里工作的一群古巴艺术家创作的雕塑装置作品。回首过去这215年的剧烈动荡,我们作为欧洲人,只能说是在不断努力,以期真正能广泛地代表今日欧洲和世界。博物馆汇聚了各国移民,还有他们所带来的新视野、新想法、新问题与新技能;而且它也为之存在。
如何解决最棘手的政治或经济问题?人们当然不能指望在博物馆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是文化上的理解、不同世界观之间的互相欣赏、不断发现历史在重大事件之外的蛛丝马迹——这些,无疑能为我们提供出路。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博物馆,仰赖我们共有的丰富历史、悲剧与胜利所赐,具有强大的力量以让我们记住:出路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