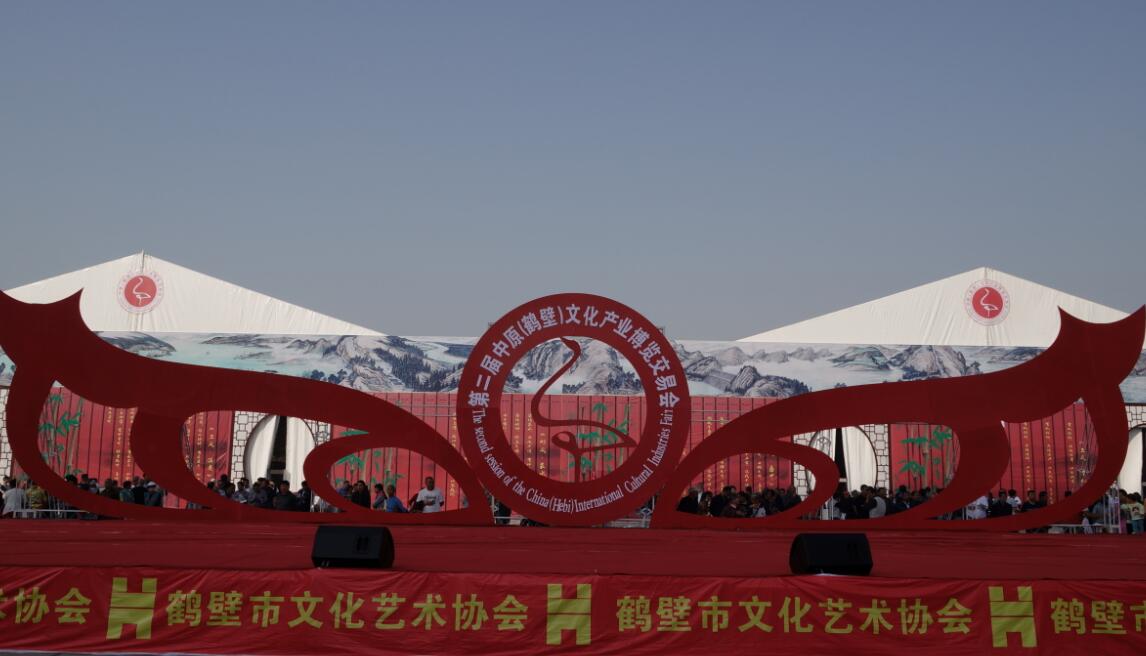一位巴西艺术家的宋瓷情结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青釉一色(圆)》(Monocromo Celadon Redondo)局部,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99×99cm,2015年,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Photo:Jaime Acioli
“巴洛克式艺术中有一种‘对空的恐惧’(horror vacui),而宋代瓷器的理念却完全相反,它在寻求空。它正是我所追求的——不是夸张和复杂,而是平静和清洁。”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1964年出生于里约热内卢,她作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巴西当代艺术家和巴西当代艺术领军人物之一,2011年以180万美元创下巴西在世艺术家的拍卖纪录。她的作品游走于绘画、雕塑、装置与影像之间,广泛取材于殖民历史、建筑遗址、剧场幻觉和世界文化等题材,在破坏与矛盾中创造出美感。
一只吸引着我灵魂的花瓶

宋汝窑青釉长颈瓶,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北宋,高20cm,R.A霍尔特(R.A.Holt)捐赠予大英博物馆
我是一个文化的痴迷者。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知道宋代瓷器是通过一本巴西社会学家利卡多·若佩特(Ricardo Joppert)的著作《青绿三昧》(Samadhi em Verde e Azu),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宋代瓷器制作的全过程和它的艺术理念,图片和文字中宋代瓷器的美丽与精巧给我带来非常震撼的第一印象。其实我很早就是一个“中国迷”。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练习过太极拳和少林功夫,那时我对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充满了狂热的好奇,还尝试着学习中文。就当我如饥似渴阅读和学习一切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之时,宋代瓷器出现在我的眼前。
不久后当我到英国伦敦旅行,走进珀西瓦尔·大维德(David Percival)的收藏展(当时在我看来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宋代瓷器展览之一)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些精美艺术品的真容。再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来到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利用那次机会,我亲眼见识到了更多精品瓷器。
我始终记得中国之行里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那是在上海博物馆的一场展览中,我久久地站立在一只宋瓷花瓶面前的样子。那一刻的我就像是一个灵魂已经飘走的躯壳,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想我的灵魂附着在那只花瓶上了,也不知道站了多久,直到保安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忍不住走过来叫我离开。
直到现在,在做一些有关艺术的分享和演讲时,我还是会专门将宋代瓷器提出来,我实在是太喜欢它了。不仅仅是喜欢,实际上,宋代瓷器中的一些元素在我的工作中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羔羊颂》(Agnus Dei),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195×205cm,1990年©Adriana Varejão
被过滤的分子

宋天青釉汝瓷葵花洗,直径13.5cm,香港苏富比,拍卖时间:2012年4月4日,成交价:HKD207,860,000
瓷器不是在宋代才被发明的,但宋代是瓷器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当时有五种类型的瓷器最受欢迎,分别按窑址被称为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瓷器,也被叫作宋朝的五大名窑。在这些有名的瓷窑中我最喜欢的是汝窑,因为它很简单,同时又很复杂。
汝窑瓷器的造型很朴素,没有太多的花样,在简单的造型之上分布着非常细微的裂纹。它是柔和的,包括它那低饱和度的釉色,看起来优雅、细致而温润。但它又给你一种感觉,它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怎么看也看不完,怎么看也看不透。它就像中国文化给我的感受一样。
我也很喜欢越窑的作品,它是唐代的一种青瓷,釉色呈青黄色,造型丰富。还有邢窑白瓷,它拥有一种空和净的美。但我不是研究中国瓷器的专家,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我热爱瓷器,可是我从来没有制作过瓷器。陶瓷是一种复杂的工艺,我对复杂的技术不太擅长。但我承认我无法抗拒瓷器之美,于是我把绘画当作是我的过滤器和分母,将我所热爱的瓷器转化到我自己的作品中。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天球赤道》(Equinoctial Line),布面油画、瓷器、尼龙线,油画140×160cm,整体尺寸可变,1993年©AdrianaVarejão
对空的追寻

定窑白瓷刻双鱼纹碗、双鱼纹盘(两件),中国嘉德香港2013春季拍卖会,拍卖时间:2013年4月5日,成交价:876,185RMB
我感激中国瓷器为我创作带来的影响——它们激励着我在画布上制作出裂纹。
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画布上加入许多类似油漆的“物质性”夸张元素。那时候,我从巴西殖民时期教会里的巴洛克式图案里(尤其来自17、18世纪)受到了许多启发,并将它们加入到我的创作之中。可是这种绘画令我感到很吃力。
于是当我“阅读”到宋代瓷器的时候,我立即被吸引了:它们的表面是干净的,没有任何的图案,只有龟裂效果和青瓷的颜色。
巴洛克式艺术中有一种“对空的恐惧”(Horror Vacui),而宋代瓷器的理念却完全相反,它在寻求空。它正是我所追求的——不是夸张和复杂,而是平静和清洁。
1990年,我尝试画了一幅叫作《羔羊颂》(AgnusDei)的作品,那是我第一次运用非常干净的表面去创作作品,也是我第一次运用来自宋代瓷器的龟裂纹理。从那时起,我开始将这种元素引入到我的更多作品之中:在1991年作品《鱼的奇迹》(Miracle of the Fish)、1993年作品《天球赤道》(Equinoctial Line)、1996年作品《肉与法兰斯邮报》(Meat a la Frans Post)和2000年作品《板上帷幔的仿古瓷》(Tilework of valance over plates)等创作中,我都使用了瓷器中的图案元素。它们也集中呈现于2015年10月我在香港展出的新作。
与宇宙的对话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cm、口径18.5cm、足距16.9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高4cm、口径18.5cm、足距16.9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cm、口径17.1cm、足径7.7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汝窑天青釉碗,高6.7cm、口径17.1cm、足径7.7cm,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我看来,“裂纹”是宇宙与我们说的话。
在瓷器工艺发展的早期,裂纹被认为是一种“缺陷”,是烧制中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残次品。但是在宋代,它逐渐被人们所理解,并慢慢演变成了一种审美思想,多么奇妙啊!
文字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甲骨文成熟于殷商时期,有考古资料发现它在商朝以前就已经存在),甲骨文的原理就是人们对龟甲上的裂纹进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种表意文字。中国的文化里拥有这种“裂纹”的基因,通过“阅读”裂纹来获得含义,这个想法让我为之着迷。
我一直认为,正在形成的表面裂纹是一种天然的、宇宙的图案。它不是由我或者任何人创造的,那双描绘它的手,也画出了人身体的血脉,画出了天空中的闪电,画出了植物的根须。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它是那么费力而又不可捉摸——那就是看着画布静静地躺在地板上,而我在等待它们干裂的阶段。
这是一个十分漫长,而又得不到任何即时反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几周,完全取决于我运用了多大规模的裂纹在我的画布之上。
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作者,我没有任何对结果的控制权,我所做的,只是等待和观察。
很多时候,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概率,我会失败,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让我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有时结果是惊人的,在一些作品中,我会得到由几条长线条形成的裂纹,而在另一些作品中,细小的锯齿和裂纹形成在整个表面上。
因此,我工作室的学徒时常会和我开玩笑:它们不依赖于我们,它们取决于宇宙。
裂纹是宇宙的作品,而我们可以“阅读”它们。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青釉一色》(Monocromo Celadon)局部,
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99×99cm,2015年,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Photo:JaimeAcioli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青釉一色(圆)》(Monocromo Celadon Redondo)局部,布上油画颜料与石膏,99×99cm,2015年,Courtesy the artist and Lehmann Maupin,New York and Hong Kong,Photo:JaimeAcioli
可选择的历史

阿德里阿娜·瓦勒亚(Adriana Varejão)《肉与法兰斯邮报》(Meat a la Frans Post),布面油画、瓷器,油画60×80cm,整体60×150cm,1996年 ©Adriana Varejão
2015年10月,我的一些作品来到中国香港展出,这些作品借鉴了很多来自亚洲的传统文化元素,特别是来自于宋代瓷器、宋代绘画,还有一些来自日本春宫画的元素。我喜欢在我的作品中融入文化扩张与演变的过程。
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作为一个巴西艺术家会如此着迷于亚洲传统艺术中的元素,在我看来,艺术让我们探寻过去与现在,这是艺术家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过去,因为没有一个冰冻在那里的真理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
我们口中的“历史”只是一个由常规看法组建起来的版本,通常为大众所知的版本都是具有偏向性的。但是,我们只接受这个版本是正确的。我们把它写进教科书让孩子们学习,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物品之前,先阅读它挂上墙上的说明,以便在我们能够产生自己的看法之前,脑中已经有了一个“看法”存在。
而我的历史观不是线性的,历史是一个互相影响的组织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构建和选择其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身份。历史是被我们创造的,这个创造基于现在。
我很喜欢一个概念,叫作“文化相食”(Cultural Anthropophagy),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文化之间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进而慢慢演变。有时弱势的文化会被强势的文化吃掉,有时候野蛮的文化会拥有坚韧的力量,反过来影响强势的文化。
中国的宋代时期是公元11世纪,据我目前所知当时中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的商业路线,巴西甚至还没有被发现呢!而宋代的瓷器文化却可以在某一天影响到巴西,影响到我。
巴西现代主义诗人奥斯瓦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在1928年曾写下《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ofágico),他说:“所有我不拥有的东西都是我感兴趣的”。这就是文化演变背后的真相吧!有一个历史版本说,巴西被发现于1500年,那么在此之前,巴西又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呢?
文化的融合和演变是必经的过程。我们是我们自己,但我们可以希望成为任何其他人。
在现代社会,我们创建起良好的沟通效率,你可以轻易地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可以变换身份,甚至进行种族的迁移。最终我们将在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高度混合的文化形态,我期待看到它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奥斯瓦德·德·安德拉德的一首小诗,以它作为结尾,因为这就是我一直想要表达的:
当葡萄牙人
在残酷的雨水中抵达
他们为印第安着衣
多么可惜呀!
当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印第安将会
脱下葡萄牙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