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他乡的你,是否还装得下那座老屋
| 老屋空了。可能,很多人的记忆里都有这样一个老屋,老屋里住着一个老人。只是,关于老家的这些形象早已模糊不清。细细品味作者的文章,也让我想起来自己的爷爷奶奶和他们住过的老屋。 |
红色的树叶纷纷飘落时,奶奶走了。奶奶一走,老屋就空了。
空空的老屋里再也不会生长出新的故事来。萋萋的荒草将在老屋的房檐上生长,远方飘来的种子将在老屋的院子里扎根,唧唧喳喳的鸟儿将在老屋的窗棂边啼叫,无家可归的猫儿将在老屋的角落中睡觉。然而,对我们来说,老屋终究是空了。

那天夜晚,我们都聚集在老屋中守灵,奶奶的灵柩就停在老屋中央,一盏不太明亮的白炙灯泡挂在老屋房顶,屋中的一切都昏昏暗暗、朦朦胧胧的。
婶婶用新鲜的棉花搓出一条长长的灯芯,姑姑找来一个光净的白瓷碗,倒入半碗油,把灯芯蘸了油,点燃,放入碗中。我们就做好了长明灯。长明灯放在灵柩的一头,草席子和旧褥子铺在地上,我们席地而坐,我们要守着这盏灯,这是灵魂的秘密场所。
屋子里的老式木门早已拆下来了。傍晚的时候,我们先是将门框上的竹制门帘取下。那门帘初夏之时便已挂上,隔着门帘,我们看不到老屋里面的光景,奶奶却能够在屋内看到外边的变化,树叶变绿了、更绿了,变红了、变黄了,奶奶看着看着,便知道时间就那样一直往前跑着。然而,现在,终究什么也没有了,门帘内外都只是空空的白和漠漠的黑了。
门帘上还挂着一个铜钱一样的小铁环,那是奶奶很早以前挂上去的,如今看看,竟没有生锈。我们把它取下来,用一块小手绢包起来,像奶奶总把那一点点零钱用小手绢包起来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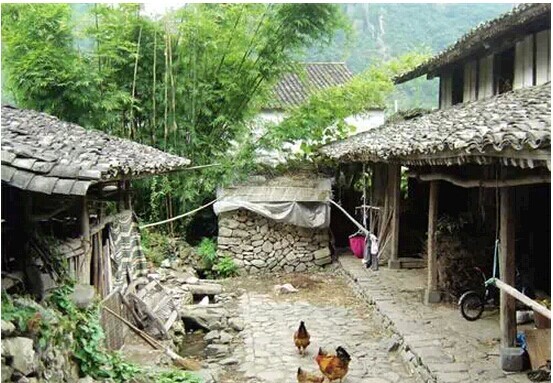
老式的木门并不难拆。木门老了,作为一扇门来说它已经存在的很久了。它不再是从前光滑厚重的样子了,它开裂了,裂纹很深,裂开的地方就像老人的皱纹,裂纹从光滑的木头上长出来,皱纹便从光滑的皮肤上长出来。
我们轻轻拨动门轴,往旁边用力一拉,老木门便从门基上掉下来了。我们撕掉了上面早已褪色的年画,伴随着掉落的花花纸片,灰色的尘土也扑扑簌簌落下,关公和秦琼的眼睛都掉进了尘埃里。我们把木门靠着墙放好后,并不走开,像怕它会翻倒一样又看了它一会儿,我们知道,再也不会有那样一只布满的皱纹的手来抚摸它了。
那天晚上,老屋是和天地相通的,是向整个世界敞开的。漫无边际的黑夜想要涌进老屋中来,携卷着树叶的冷风也想闯进老屋中来,我们都不阻挡。我们坐在灵柩旁边,用微微发凉的双手守护着长明灯那跳动的火苗,把红肿的眼睛望向黑夜中某一个坍塌的点,任凭那种叫做夜枭的鸟儿在心中啼叫。

老屋越来越空了,八仙桌和条案也被抬走了,中堂也被卸下来了。这一套东西曾经是老屋的核心,也是那古老文明的延续。曾经,中堂里藏着一个世界。墨绿色的松、鲜绿色的竹、浅黄色的菊和殷虹色的梅,它们构成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画,挂在墙壁正中央。“有径鸟自来、无风花奇香。”这样一副颇具哲学意味的对联挂在画两边。这不像穷苦的农村家庭该有的东西,然而它就那么存在了许多年,并且成为我懵懂的童年生活中永远的难解之迷——鸟的身体长在天上,为什么要走路过来?既然没有风,花的香味怎么会飘过来?
初学识字的我把这两句诗反复“吟咏”着,直到条案上那架老座钟开始“当当当”报时。老钟,是的,大概每一间老屋里都会有这样一座老钟吧,比博物馆里那些带着贵族气息的老古董座钟要简陋的多,通常只会有一个木质的钟座和一个圆圆的表盘,表盘下面挂着一个圆形的钟摆,顶多钟座上方再装上一个马踏祥云的小雕饰,除此以外,便没有什么了。

然而,这就够了。对于刚刚记事的小孩子,只要有了这样一座钟,老屋中那漫长的时光便会流逝的快一些。“当当当,”这是可以数数的时光,也是可以期盼吃或者玩的时光。只要钟声一响,我便习惯跟着扳指头。所以,也最怕那声音突然停止。
于是,我开始给老钟上发条。这本是爷爷奶奶的事情,我小时候却常想试一试。打开钟座上的玻璃门,拿起钟摆下方那把钥匙,轻轻插进表盘下面的小孔中,“咔哒咔哒”,一圈又一圈,这竟成了一件让小孩子着迷的事情。这老钟在我的折磨下,越走越起劲了,有时候我去和爷爷奶奶一起睡,睡前总能听到老钟的报时声,特别响亮。“当当当”,黑暗中的老钟像是在赠送什么礼物。不过,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有响声了。或许,夜半的钟鸣声都钻进了我奇奇怪怪的梦里。只是,不知道它是否打扰了爷爷奶奶的睡眠?
现在,老钟早已不见了,我甚至都没意识到它是何时不见了。就像我没意识到爷爷奶奶是何时开始白发苍苍一样。一切,都像时光一点点流逝一样,渐渐地改变了。

在那个凄凉的守灵之夜,我们把一大块白色的布挂在墙上,挂在原来中堂的位置。在火光微弱的长明灯旁摆上香炉,摆上贡品。爸爸点上四根长长的香,放在香炉之中,我们叩拜,然后在心中默默祈祷。
我们不再需要钟表了,不再需要被分隔的时间了,我们就这样守着一炷又一炷香度过这个凄苦的长夜,就像奶奶守着那火苗如豆的煤油灯度过漫漫长夜一样。
等到奶奶的灵柩移走以后,老屋便会更空了。即使那张漂亮的八仙桌再抬进来,也没人再用了;即使那两把漂亮的太师椅再搬进来,也没人再坐了。以前,八仙桌上铺着蓝白色的桌布,蓝色是天,白色是仙鹤,仙鹤还有红红的嘴、黑黑的脖子和黑黑的脚。仙鹤的腿长,我曾经想它一到晚上就会悄悄地从桌布上溜走,迈出长腿来能一下子攀到屋顶。

然而,我的故事太幼稚,我还是喜欢听爷爷讲。通常是晚饭过后,爷爷会坐在他的太师椅上讲“没尾巴来成”的故事。一个叫来成的年轻人,平日里规规矩矩,然而一到月圆之夜就会变身,头变长、耳朵变小、嘴巴变大、牙齿变尖、全身都长出毛来,嗷地叫一声就变成了一只狼,只是不长尾巴而已。变了狼的来成专门跑到村子里吃人家的小孩子。
一般情况下小孩子总是睡在大人中间,尤其冬天还包裹的严严实实,然而来成从窗子跳进屋中后,却总能踮着脚跨过大人的身躯,独独把那紧紧挤在中间的小孩子叼走吃掉。等天亮大人一看小孩不见了,都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觉得是中了魔。
爷爷每次讲到来成进屋跨过大人去叼小孩子的情景时,便会突然往前欠一下身,半趴到八仙桌上,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用一种神神秘秘的语气问我:“你想呀,那小孩儿都夹在大人中间,来成是怎么把他偷走的?”我当然不知道,而且觉得好诡异,都不敢扭过头去看窗子,只怕也有一只幽灵般的来成进来。爷爷看到我神情紧张,一会儿便会笑起来,仿佛用那笑声就能安慰我似的。也果真如此。奶奶就半躺在东边的太师椅上,眯着眼睛听。

可这终究是遥远的事情了,故事的模样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在那个凄凉的守灵之夜,我望向外面无边的黑暗,竟然也记不清楚爷爷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结尾了。只知道自己已经流下泪来。
然而,那个夜晚,那个守灵的夜晚,其实我们都没怎么回忆。我们害怕回忆的伤痛,就开始做一点能让自己一直着忙的小事情。比如叠元宝,不停地叠,就像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最后,我们把叠好的元宝做成金山银山,烧给奶奶,奶奶在那边,再也不用担心没钱花了。
我们知道,这金山银山会变成灰烬,飘在空中。我们也知道,这几十年里,老屋生长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早已飘散到每一个人的记忆海洋中去。
然而,奶奶一走,老屋也走到了时间的终点,所有的故事都要终结了。老屋,终究要空了。
作者简介:夕西然80后,生于豫北乡村,现供职于郑州某事业单位。业余读书人,愿以柔软之心书写日常生活。














